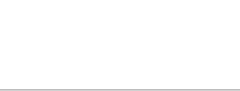不忘全球化初心,牢记为中国使命。
文丨华商韬略 陈斯文
如果有人在1999年7月10日中午身处洛杉矶玫瑰碗体育场,他会面对39℃的高温,看见一头金发的美国第42任总统克林顿,聆听90185名观众爆发出的欢呼。然后见证4架F16战斗机从头顶掠过,所有的感觉都彻底淹没在声浪中。
除了气温,这一切都属于克林顿主导的大戏,剧本主题只有一个关键词:修复。
过去的两个月,中美关系降到了冰点。贝尔格莱德的三颗导弹,不仅击穿了中国大使馆的屋顶,也打断了入世谈判的步伐。在克林顿的致歉电话被拒绝后,美国大使馆门口聚满了示威群众。主打留学培训的新东方,业绩损失堪比日后双减,北大学子则打出了一句口号:
“不考托,不考G,一心一意打美帝。”
如何化冰点为拐点,既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,也需要恰当的时机。等待了两个月后,克林顿等到了他要的机会。
1999年的美国女足世界杯,中国女足连胜5场,传奇中场刘爱玲用两粒世界波,轰得挪威门将呆立原地。闯进总决赛后,对手正是美国队。
这真是一份天赐良机,有尼克松和周恩来的“乒乓外交”在前,晚生后辈克林顿决意效法。他安排空军表演、亲临现场观战,在目睹了误判与点球大战后,在第一时间来到中国女足休息室,向中国表示了祝贺:
“整个美国都被比赛深深吸引住了,女足世界杯所产生的巨大影响,超出了人们的想象,这种影响不仅作用于美国,也作用于其他国家。”
小球再次转动了大球。克林顿的甜蜜赞美,化开了中美关系的坚冰。但当战斗机掠过天空时,却少有人注意到场边的一块块广告牌——可口可乐、宝洁、麦当劳、通用……站在这些广告牌后面的,是那些跨国公司的领袖们,他们同样等待着一个表达友好的机会,向他们向往的中国。
【01】
在克林顿的背后,是来自美国工商界的巨大压力。
3个月前,中国总理朱镕基为WTO谈判而来,在争吵8天后又空手而归。这惹恼了几乎所有大公司,他们派出可以自由出入白宫的掮客,轮番轰炸克林顿的经济顾问斯珀林。然后派出记者,直接轰炸总统本人:“他入主白宫最后悔的事有两件,一件是勾搭了莱温斯基,一件是拒绝了朱镕基。前者证明了总统的无耻,后者证明了总统的无能。”
这不是美国产业界第一次为中国问题向政府发难。上一次发生在1993年,原本无条件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,变成了“需要与一些问题挂钩”。
于是,298家大公司和37个贸易团体共同致函总统,要求美国政府无条件延长最惠国待遇。立场背后是现实的利益——1993年,中国进口美国商品的总额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,并且仍以30%的速度快速增长。
波音公司充当了挺华急先锋,暗地推动华盛顿州的一名众议员,发起了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公开信,获得了160位众议员的签名。当然,这离不开中国120架飞机、价值90亿美元的大订单。
1999年的形势远非昔比,中国的开放程度与日俱增。如果谁还在用“在华办事处”和空投的“首席代表”试水生意,这玩法一定会让人笑掉大牙。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》已经颁布了五年,跨国巨头可以在合资企业里控股,可以把利润并入母公司的财务报表,向股东描绘新市场的华丽增长故事。
中国区取代了办事处,“大中华区”、“东北亚区”这些遮遮掩掩的说法成了老皇历,会说中文的新加坡人和香港人取代了欧美高管。苏州的高新区向APEC成员国开放,新名字叫作亚太科技工业园。德国车正加速从流水线上驶下。法国人早就在天津和上海建起了工厂,在最新的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,管委会成了低压电气工厂10%的小股东,并提供从招工到上门办税的一揽子服务。
花旗银行的中国区总部从香港搬到了上海,戴尔在厦门建立了第一个生产基地和服务中心,宝洁一口气在中国建立了4家公司和5座工厂,福特公司主管国际业务的执行副总裁韦恩·伯克说:“我的头号业务重点是中国。”但美国人仍嫌速度太慢。在通用电气,有位副总裁学会了一句诗词,得意洋洋地在同僚中传播。那句诗叫作:“一万年太久,只争朝夕。”

在跨国公司的董事长们看来,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市场,是每一家跨国公司都应该去的地方。
从1979年至2000年,中国累计吸引外资3462亿元,大部分是1992年以后发生的,1992-2000年的累计流入量,占总量的93%。
但所有人仍嫌太慢太少,尤其是身为第一大经济体,拥有最多跨国公司的美国。
柯达的总裁裴学德算过一笔账,很能反映这种梦想的迫切。“只要中国有一半人口每年拍一个36片装胶卷,已经足以将全球影像市场扩大25%。中国每秒多拍摄500张照片,便想当年关于多了一个规模等同于日本和美国的市场。”
用人口乘以某种商品,然后计算出中国市场的规模,再加上乐观或保守的PE增长率,这几乎是所有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时的通用算法。
所以当克林顿送出甜蜜赞美,加上《财富》杂志奉上的全球财富论坛邀约。所有人都认为好事成双,机不可失。
包括杰克·韦尔奇在内,三百多位董事长、总裁与首席执行官急匆匆地调整了行程,他们从东中国海进入上海的空中走廊,奔赴梦想中的奶与蜜之地。
等待他们的是一场真正的高规格年会,刚刚落成一个月的上海国际会议中心被选作会址,二百位中国最大型公司和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列席,年会的主题是“中国,未来五十年”。但重要的是江泽民主席的亲自出席,面对全球最显赫的工商业人士,他的演讲题目是《你们把眼光投向中国,中国欢迎你们》:
“中国企业要学习外国企业的先进经验,走出去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经风雨见世面,增强自身竞争力。当然,中国政府将为来华投资的外国企业提供良好的条件,创造更好的环境。”
这是一段巧妙的发言,它传递了合作的意愿,又彰显了自己的目标——绝非卑微的乞援,而是真正的东道。
江的话不出意外地赢得了雷鸣掌声,显然,在座的商业领袖们听进了后半句。于是在第二天上午的大会上,当他们谈起各自的全球战略和投资策略时,看好中国成了共同表态。美国人尤其热切,百事可乐董事长表示“要让每个中国人喝一罐百事可乐”;通用汽车总裁判断“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”。《财富》杂志的编辑最后一锤定音:
“欲独霸世界,先逐鹿中国。”
这是一个宾主尽欢的时刻,在9月27日的晚宴结束后,浦江焰火,明照东南。中国摄影家刘香成后来回忆说,那是他一生中看过绽放时间最长的烟花。
【02】
在上海三日里,杰克·韦尔奇讲过一段话:“我对中国很陌生,但我相信它会很强大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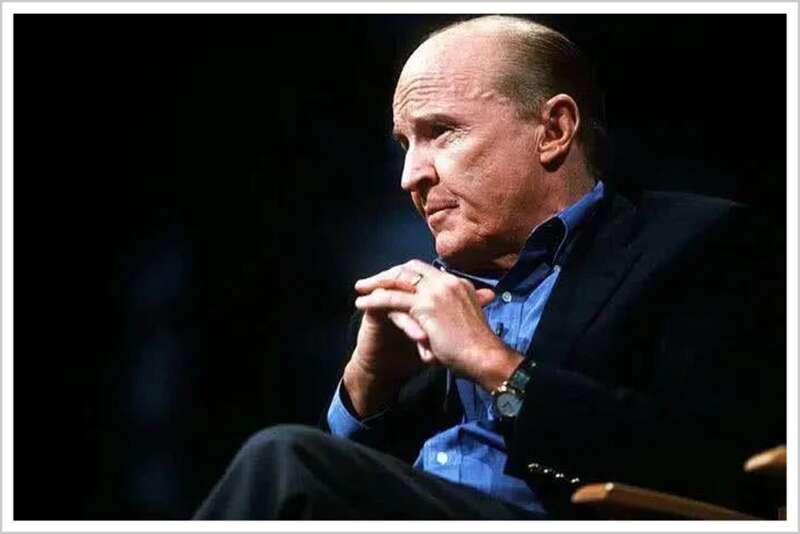
杰克·韦尔奇
从日后发生的历史来看,在面对中国市场时,跨国巨头表现出的生疏,以及中国展现的强大,都被杰克·韦尔奇言中。
入世的谈判在北京落槌,海外资本从全球涌向中国。当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之初,似乎全世界都认为它们将凭借技术和管理优势,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赚得盆满钵满,在与中国企业的竞争中获得全胜。
但现实并不支持这种过于乐观的想法,裴学德的“柯达算法”很快被证明为“如果每人给我一块钱”式的乌托邦幻想。前《华尔街日报》记者麦建陆在《十亿消费者》一书中写到:“我看到,众多的西方管理者充满信心,飘飘然地来到中国,结果却被他们的中国竞争对手、中国政府或中国合作伙伴碾倒,要么就是陷入不切实际的预期,急躁和缺乏常识中。”
从影响克林顿政府到影响小布什政府,所有跨国巨头都抱着一门心思——把制造环节搬到中国,靠近全球最大、增长最快的市场,多赚很多钱,再将这些利润投入位于美国的研发部门,不断创新和提升竞争优势,最终获得全球性的竞争力。
这种心思贯穿始终,但把它放在“跨国公司和中国成长”的话语环境中,却需要不断增添新的内容。
灵活的跨国公司很快发现,他们自诩的先进管理经验与商业模式,需要进行本土化的改造,方能在中国市场上取得“1+1>2”的效果。
这种本土化,不是从中国区总裁从“Peyton”到“庞中华”的改名,不是操着塑料普通话的新加坡高管。不是西装革履、要求飞机往返的美国销售经理,不是从美国工厂运来整个开关柜,只由中国工厂装上最后一块挡板的生产方式。
中国市场大门洞开,但却需要充足的耐心。如果做不到“制造在中国”与“研发在中国”,那么“销售在中国”就会变成哈德逊河上的泡沫。
于是可以看到,那些名牌院校的中国毕业生,逐渐在外企里获得了独立办公室和总监头衔;从夫妻店起步的贸易公司,开始被纳入外企的分销商体系;来自底特律的品控工程师,开始和中国管理者一起寻找本土供应商,那些街道小厂接到了外企订单,尝试性地生产零配件,去实现外企的国产化替代。
一家挂着“精密机械有限公司”牌子的小工厂,接到了电气企业的螺丝订单,但它立刻发现自己身处残酷的奥马哈海滩:国标的废品率是千分之一,工厂只能做到百分之二,而采购者的要求是万分之一。
美国工程师走进了工厂,也把“六西格玛”这样的词汇带了进去。这种国产化替代的尝试费力巨大,供应的螺丝总量只能装满一个饭盒。但随着废品率的下降,中国螺丝便取代美国进口,一饭盒变成了一板车,又变成了一卡车。二十年后,那个小厂拥有了十万分之二的废品率,变成了一家年销售额八十亿的公司。
种下规模化和规范化的种子,收获一批便宜又好用的供应商,跨国公司拥有了稳定本土供应商体系,和整个产品成本的下降。这都帮助公司在市场上增加了竞争力。同时,这种先进的生产体系,也让中国供应商拥有了与国际接轨的生产水平,可以为更多采购者提供配套服务。
中国因此拥有了深圳、东莞、义乌这些世界工厂,有了东部沿海地区发达的制造链。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徙——春运。在承接美国产业转移的同时,中国其实还得到了更多: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,强大的基建能力压低了生产要素价格,本土公司在与外国对手的交锋中,学会如何掌握从精益制造到研究消费者需求。
如同一个并不显眼的、却不可或缺的零部件,那些跨国公司嵌入了庞大的“中国制造”产业链条。在经历了“制造在中国、销售在中国、研发在中国”的三部曲后,跨国公司口念心奉的信条变成了“在中国,为中国”。
北京望京科技园,原本是科技部和北京市政府试图打造的全球顶级电子公司中国基地。摩托罗拉、北电网络、索尼爱立信、三星、朗讯云集于此……在中国市场,它们有的曾经如日中天,最后又在生死线上挣扎,有的由弱渐强,成为了中国经济成长的获益者。

对于那些学会如何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而言,这个市场给了他们想要的东西。默沙东2021年制药业务收入超过427亿美元,同比增长17%,中国区收入超42亿美元,同比增长60%;礼来中国区收入增速,是全球营业收入增速的三倍;
霍尼韦尔在中国雇佣了13000名员工,在上海制造航空电子设备,在苏州生产加热系统,在南京制造医疗传感器,在天津生产工业控制系统,在武汉制造汽车涡轮增压器。从“鸟巢”的广播系统,到西安兵马俑博物馆的消防安全设备,都出于这家公司之手。这些面向全球市场的产品,共同构成了它2021年343.92亿美元的销售收入。

霍尼韦尔西安工厂
变化快得令人目眩,谁能想到,在霍尼韦尔建立北京办事处的1980年,它甚至还不知道该把自己的产品卖给谁。
【03】
2020年10月,三只巨大的箱子运进了特斯拉的上海临港超级工厂。随后,它们将变成一台长19.5米、高5.3米,重超400吨,相当于5架航天飞机之和的超级机器。
有了这台机器,焊接1000次以上、耗时两小时的传统车架生产流程,只需一次2分钟压铸,同时也为特斯拉的Model Y省下了20%的成本。
在投资中国的道路上,依靠上海工厂翻身的新钱马斯克,要比当年的老钱更豪迈。但这谈不上“长江后浪推前浪”,只不过是后来者对前辈的模仿。在自身飘红业绩、中国持续开放的感召下,美国的跨国巨头们达成了新的共识——更有意愿和信心深耕中国市场。

上海美国商会和普华永道中国在2021年9月做了个调查,在338家受访公司中,78%表示对本公司未来五年的业务展望感到“乐观或略微乐观”,比上年同期高近20个百分点;感到“悲观”的企业占比则下降了8个百分点。
更鲜明的态度,来自于另外一组美国企业的投票——有60%的企业仍然认为,中国是其近期全球投资计划的前三大投资目的地之一;66%的企业计划今年增加在华投资;83%的企业没有将制造或采购转移出中国的打算。
所以我们会看到,在美国投资中国市场的历史中,“挂钩破产”、“台海危机”、“领袖互访”、“大使馆遇袭”……有太多的扰动因素,让美企中国区这项“共同的事业”遭遇坎坷。但在对华投资的美企中,却只有市场竞争的失败者,绝少地缘政治的站队者。
所以我们会看到,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反复施压的几年里,跨国巨头们却选择了缄默不语。
所以我们还会看到,尽管太平洋两岸磕磕绊绊,数据却在大唱反调——2022年1月中国吸收外资额同比增长11.6%,增速接近去年同期的三倍。在前四个月里,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增长了53.2%。
数据只会默默记录事实,却不会说出中美各自的心里话——如果世界最大的市场和最强的科研中心渐行渐远,对双方乃至全世界,都会是巨大的损失。毕竟,中国在基础科研质量、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等方面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美国想要在全球再找一个巨大的市场,南美不行,非洲也不行,没有了市场,美国公司持续不断的高额研发支出很难持续,也就难以长久维系技术优势。
在这一点上,企业背后的资本是西方,还是东方,其实不应该是一个过分纠结的问题。
世界上从来没有抽象理论中畅通无阻的市场。市场从建立到完善,其规模和效率都需要逐步提升。完善的市场,从来都是经济发展与政府呵护的结果,而不是前提。
中国成功创造了自己的模式,它借用了一些西方的想法,同时也拒绝了一些想法,它在必要的时刻向世界开放,在适当的时机踩下刹车。这是《纽约时报》对投资中国的总结,但用我们更熟悉的语言来表述,应当叫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
两个大国的相处,总是需要包容的智慧、开放的态度、共赢的思维。这一点,历史已经无数次给过答案。2016年9月,在与美国经济金融界座谈时,李克强总理曾经用一句话总结过中美关系,他说:“中美建交40多年,尽管期间不断出现过风风雨雨,但总是雨过天更晴。”
但总理还有后半句——“当然,我并不主张非要下雨才带来晴空。最好是少下雨,或下小雨。”
【参考资料】
[1]《中美关系史》陶文钊
[2]《外交十记》钱其琛
[3]《朱镕基总理决断中美谈判的故事》赵忆宁
[4]《1999,中美逆转的48小时》饭统戴老板
[5]《中国为何成跨国公司业绩亮点》美中国际商会
[6]《1999年上海全球财富论坛回顾》人民网
[7]《激荡三十年》(下)吴晓波